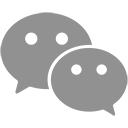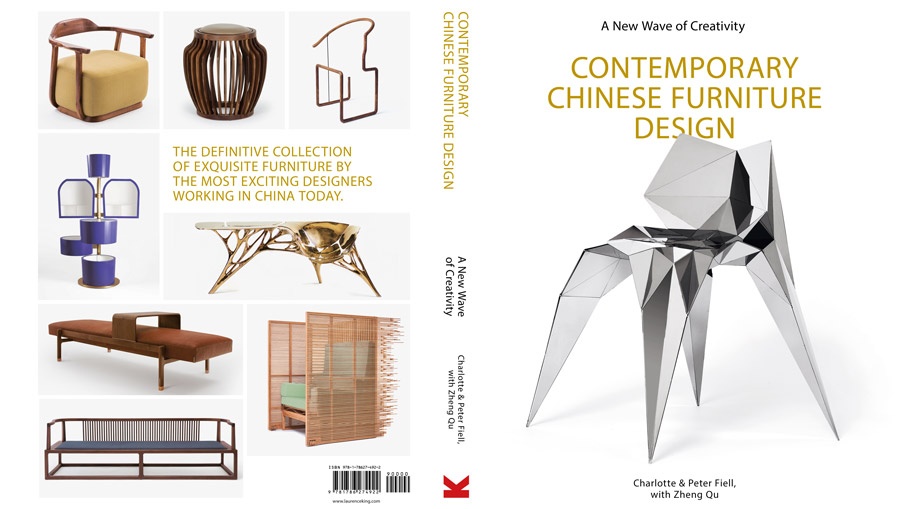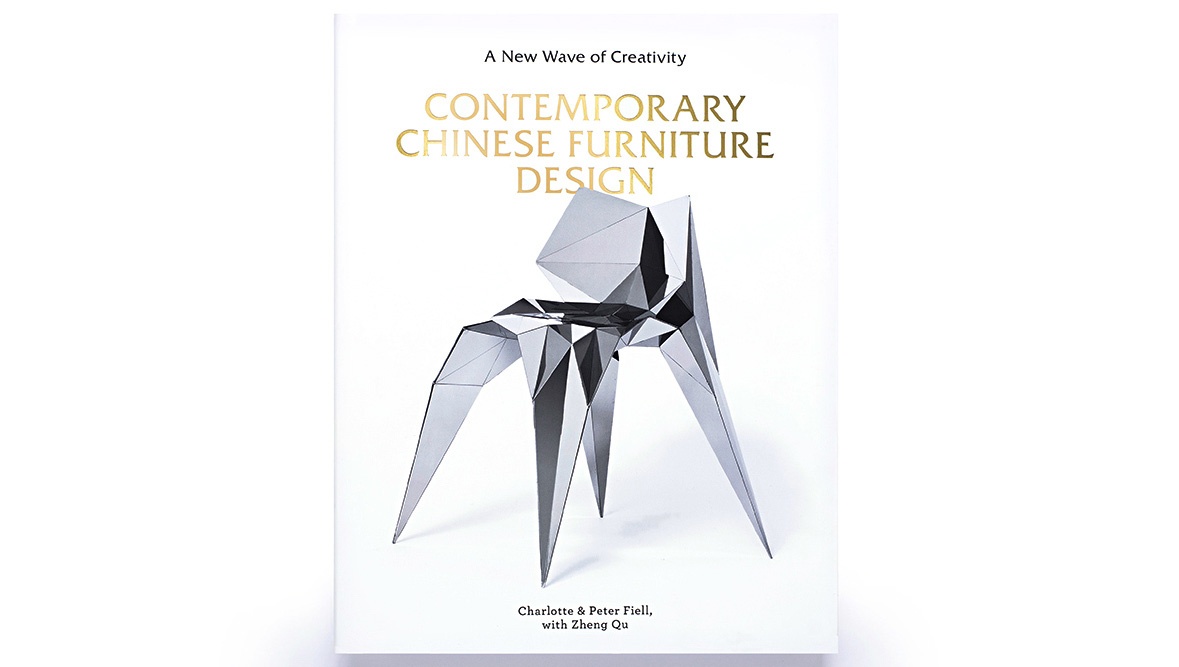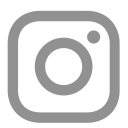占晓芳是兰卡斯特大学设计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及兼职讲师,也是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她的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性设计、工艺文化及造物哲学。2018年,她去中国景德镇进行了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建筑/设计/时尚部的“手工创造未来”的研究,该项目主要通过对当地手艺人和艺术家、设计师之间合作模式的研究,探索设计在手工艺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与贡献。 “手工创造未来-陶瓷手工艺的协同设计研究”项目还得到了英国手工艺协会、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支持。
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短片——《手工艺未来:景德镇》
以下为伦敦《Disegno》设计杂志对占晓芳就“手工创造未来项目”的采访及总结,中国设计中心在占晓芳的帮助下进行翻译整理。
为什么要研究手工艺呢?相比其他的偏远乡村的手艺,你为什么要选择景德镇作为研究案例?它可以给英国提供什么经验?
因为手工艺的创造性及复杂性与设计的本质其实是十分接近的,这可能比较自然,我之前的背景是基于本土文化的视觉和产品设计。在我以前对景德镇的手工艺案例的研究中, 我看到一种不一样的生态,那里的工匠以前基本都是跟本土的传统艺术家合作,现在合作的对象就更广泛了,外来的艺术家/设计师, 本土的艺术家/设计师等各种创意人员,最主要的是它的规模和形式。当然这种合作现象并不新奇,但艺术人类学教授方李莉老师说:“能够在当代形成一种基于手工技艺的产业化的混合模式,这在全世界的手工艺发展史上并不多见。”当然这有中国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英国的Stoke-on-Trent (英国的瓷器生产中心), 他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手工业体系,甚至工业都近乎解体(尽管近十年有回归);当然在设计领域,也有很多关于东南亚和东欧一些城市手工艺的一些研究,但基本都是怀旧的基调,反思后工业化设计产业模式。再有就是艺术家、设计师进驻发展中国家的偏远乡村的参与性设计/艺术干预行动等,当然这些非常有价值,而且是有可论证的确定性价值。然而那种直根于自发、偶然、有时候看似“混乱” (借用一下我导师沃克教授的词)的“有机”的合作却充满“不确定”。很多西方的研究者对景德镇充满憧憬,但又免不了批判她的“工业性”特质。当然这种印象在西方研究者那里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手工艺”这个词所代表的观念,自理查德·桑纳特(Richard Rennett),蒂姆·英格尔德(Time Ingold)和特雷弗·马钱德 (Trevor Marchand)等人不断的诠释中已严然变成对抗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的异化、原子化、集中化弊端的解药。

占晓芳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协同工作坊
这里有很合理的一面——手工艺是整体的、参与性的一种造物方式,但是手工艺生产的本质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为什么没有研究者去研究手工艺“分离性” 的这一面,不去挑选这一面表现强烈的工艺去做研究呢?其实这种特质从青铜手工艺开始就存在了,虽不能说是被工业化污染的产物,但芝加哥大学的马丁·鲍尔斯的书里面就说明过中国汉代的青铜工艺怎么通过分离分散的分工形式,控制人的独立创造性,从而分散社会权利。还有很多建筑保护领域仍在使用的传统石匠工艺,其实也是没有所谓的完全的“整体性”的,他是“参与性”和“分离性”的结合。
手工艺可能没有那么纯粹,不能对一种生产方式的弊端寄希望用另外一种逝去的方式来完全克服,总是对立起来,说手工艺就是人性化的造物方式,而工业化是非人性化的。再要讲可能就要说到西方传统以来、现在其实还占主流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和认识论。所以,我希望通过研究景德镇这种“产业性”手工艺生产形式,知道它为什么会存在,在发展创新中有什么问题,怎么借助设计(思维)帮助它更好的存在,同时,它能给英国的手工艺发展提供什么参照。
可以形象的描述一下那边的情形吗?是什么样的一个陶瓷风景?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中断后,传统手工生产是怎么复兴的?
在我做这个协同研究的时候,正是一个湿润寒冷的冬天,这时候不是做陶瓷的理想季节。但即使是在深冬,也可以看见作坊里有很多手艺人在作画,雕刻,拉胚。磨坊溪水边的汩汩流水,渲染着那永不熄灭的窑火。这座城市还遗留千年历史的石碓,高楼林立的街道边,仍旧跑着人力大板车,工匠们在杂乱的村落作坊里一起拉着巨大的大缸大瓶,成排的刚出窑的陶罐,在改造后的旧工厂区,充满了别致的酒吧商店及画廊,还有和环境和谐相融的的乡土饭店。你能想到的元素从农业时代到西方的后工业时代,这里都可以找到。这虽然已被炒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概念。然而这不是一种被规划的景象。

一位在景德镇制作陶艺的手艺匠人
一位美国艺术家说景德镇是一座三合一的城市:农业、工业、后工业三位一体。艺术人类学研究院的方李莉教授曾评价:“当代景德镇的制陶产业既不仅仅是前工业性的也不是现代性的,而是后现代的。” 进一步的研究学习后,我渐渐了解到她的“后现代”其实大概类似目前西方在探索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这个概念虽然很宽泛,但是景德镇现象却是一个通俗的解释,我的论文里面曾称它为“后手工艺”制造。在景德镇,传统农业手工艺的模式正在和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一起在交融着复兴,而三宝国际陶艺村是这方面的先行者,陶艺家李见深希望通过打造一个“家” 的理念,来呈现除工业以外的传统手工艺模式。

占晓芳与李见深在三宝国际陶艺村
1990年中叶以来,国有瓷厂大量关闭,集中式生产模式被散布在旧工厂附近和周边村落里的私有化作坊代替。私有作坊的兼容与灵活性为传统工艺的复兴与振兴打下了基础。这些技术高超的手艺人及他们的作坊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包括大量外国艺术家与陶瓷家来合作。过去25年间,由于特殊的需求,当地工匠与艺术家/设计师的有机合作极大程度地复兴了当地的传统手工生产。不同技术与理念的融合给景德镇陶瓷工业在当代社会中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复兴与发展。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做的这个研究,有什么程序和活动吗,设计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这个项目不是以产品的当代创新为主要目的,这些对景德镇的陶瓷创新实践来说可能并不是太需要。这里的作品整体上来说已经比较成熟,这里的当代和艺术氛围已经生成了足够去消耗并且过剩的新“产品”和“审美”。这里可能更缺的是手工艺的内在价值的保护,工匠生存状态的改善,和最大限度的保护传统工艺本身及它的精神。在这种合作创造中,曾经的手艺价值,和后来赋予的手艺的当代价值是流失了还是增加了?为了深层理解“后手工艺”制造的机制与手工艺的中的合作价值,我开始了一系列访谈和协同创造的工作坊,及一个为期两周的手工艺创作实验。

占晓芳在景德镇开展工作坊
在协同创造工作坊中,我同时也检验了以前的一些假设和结果,比如利益相关人包括不同生产者,对手工艺价值的认同模式及类型等;参与者通过一系列环节提出了一些克服问题的提案,比如‘沉浸式-深入性社区参与-协同创作’;实验创作项目的目的不在于实体的产品,而在于动态观察。其实方法对读者来说很枯燥,主要是设计人类学领域的参与性行动方法和一些相关工具,它不是被动的采纳意见和观察,而是利用研究者作为促进者在行动中采集信息。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支持下, 这些合作研究很成功,使我了解了他们的教育模式并且带给了英国的手工艺界,同时通过参与性的合作性的研究,也使我也了解了合作的动态过程。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方法操作上也有很多局限。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般性结论吗?
研究结果还在整理中,我围绕之前你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跟你探讨几点认识:首先,与英国的个体主义实践不同(maker/making),相比手工艺作为一种思维、一种脱离文化地理语境的上的方法论,手工艺的知识与技能在景德镇意味着一个系统且社会化的生态,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工匠的身体里。这跟这种手艺合作模式能在地、自发性诞生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这个跟很多研究的结论也相符,从西方工艺人类学领域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景德镇的陶瓷制作发生在人/社会/地方的关系网中:如果整个社会的关系网断裂,脱离原地生态系统,这种技艺也不复存在。技艺的衍生与发展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交融中。‘地方性’是最重要的特征。这种‘联系性’其实还应该扩充到更广泛的维度:传统技艺与当代技术,旧与新,当代美学与本土文化,制作(感知)与构思(认知)。

实验项目工作坊
还有一点就是,边界模糊对设计师与手工艺人的深入交流非常有益。为期两周的实验项目证明了“生活”与“干活”的无界限融合,滋生共享文化与价值。这种后手工艺的生产合作模式,区别于正统设计教育中的手(制作)、脑(构思)的分离。这是直根于传统生产方式和创作方式中的后工业生产。置于情景日常交互中产生的理解力与同理心是关键,当然这里也不是纯粹的。

实验项目在占绍林工作室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刚在说的“等级” (hierarchy) ,这在景德镇的这种后工业式的生产模式中其实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是“有机”性存在,并互相渗透交换。这里面需要澄清概念(怎么样理解等级,在什么语境里等)。这样一个结论好像推翻了我之前的想法。红房子工作室的合作创始人安田猛先生说过,“这里的一切都是生动又灵活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宽泛的合作型的创造,更反映了一种态度与思想。手工艺的知识和技能与艺术、创意在这里同等重要。因为艺术家与设计师们,甚至年轻的陶艺家知道他们的短板与局限,他们需要依赖且尊重手工艺人的高超技巧。尽管在西方很有争议,绝大多数的工作室里都没有等级的划分。每次当工匠师傅们来工作室“干活”,整个团队包括艺术家和设计师都非常专注聆听,包括师傅给他们作品草图与想法的意见。这里的等级之分只存在于技艺、创造性专注力的差别。如果说谁要屈从于谁,那是合作者对材料和技艺的妥协。

从左至右:占晓芳、梁欣、安田猛、弗丽斯蒂·阿里芙、熊白煦|摄于红房子
在欧洲代表遗产手工艺的制作技艺和代表创客文化的创新创意有很多的交融,手工艺需要创新技艺本身吗?还有设计师和手工艺人,你觉得应该是同一个角色吗?
我的理解是在思维方式上,在英国这两种形式是不分彼此的。但对于被工业化抛弃的遗产手工艺还几乎跟创客没有什么实践和形式上的交融。我参与的几个关于遗产手工艺的研究课题,另外在英国代表先锋艺术/技术创客的Crafts Council (手工艺协会)和传承保护为主的Heritage Crafts Association之间的工作范围和领域并没有很多重合。关于传统技艺本身,传统不是静止的,传统是不断创新中的传统。尽管景德镇的多数手工艺人技艺高超,但随着创意设计产业的兴起,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平庸工匠的数量,他们的技艺缺乏前人的水准。很多受访者告诉我,挑剔的陶瓷设计师们为了做出自己想要的效果,从手工艺人那里学习传统技艺,但毕竟有限。后果就是,许多艺术家、设计师的新奇想法不得不向传统技艺妥协。例如许多优秀的画匠师傅只能创作流传下来的固定颜色与图案,却不会改变去做新的尝试。
一门手工技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在一个庞大的手工体系内,期望设计师技巧高超是不太现实的,当然技艺精湛并且及有创造力的陶艺家除外。因此,必须要唤醒手工艺人学会改变,且激发他们对新的尝试。如果不仅仅是把手工艺产业当作一个遗产资本,这个改变是有需要的——遗产资本也是需要新的血液。所以,我觉得,(又颠覆了一个理想价值观)工匠与设计师不一定必须是一体的,但给双方灵活的空间可以促进有意义,互相尊重的合作,以此来调和两者的差异。
能对你的研究做个总结吗,不仅仅是手工艺文化,从更大的范围上讲,从你的经验中,有发现中英在设计领域或者思维上有什么不同吗?
希恩(Sheehan)曾经说,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而基于这种认识论上的创新和设计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倒使问题更棘手。他说,种种失败集中反映了这种生产方式“本体论上的缺陷”。我觉得其实他也暗示一个认识论上的缺陷, 建制派方法论需要聆听多样社会的呼声,曾经边缘的和本土的现象和社会存在能够持续,应该有其自身的道理。他所呼吁的本土方法(indigenous methodologies),其实也就是指地方知识启发研究范式,这值得继续探索。



 Shop
Shop